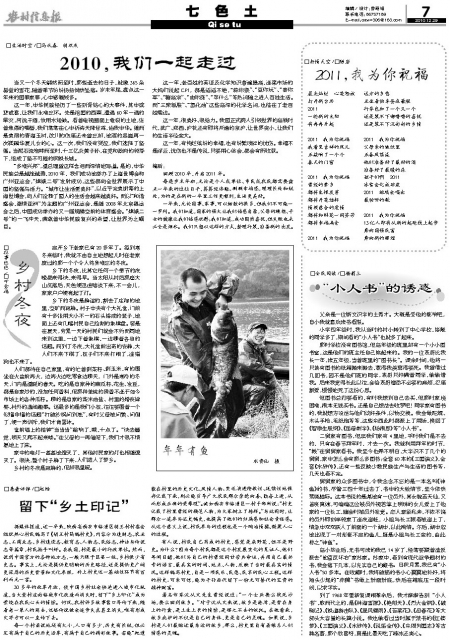留下“乡土印记”
□悬壶评弹/□赵畅
留下“乡土印记”
据媒体报道,近一年来,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胡王村村委会组织热心村民编写了《胡王村简编村史》,内容分为建制志、农业志、工商业志、乡村建设志、教育志、人物志、民俗志、神话与传说志等篇章,村民拍手叫好。在我国,村是最小的行政单位。然而,说到中国官方的各种地方志,一般只限于区县一级,乡村很少有史志。事实上,无论是提供更明晰的历史路径,还是提供更广阔更深厚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参照,补上村史这一基础性环节有百利而无一害。
30多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乡村社会快速进入城市化轨道,当大量村庄面临城市化改造而消失时,留下“乡土印记”成为萦绕在农民心头的情愫。何况,农村许多故事靠口耳传下来,随着老一辈人的离去,这些传说便会逐步失真甚至消失,唯有形成文字才可以一直传下去。
每一个村虽说地域有大小,人口有多少,历史有长短,但必定有属于自己的历史沿革,有属于自己的精彩故事。若能“把遗散在村里的历史文化、风情人物、变迁演进抢救性、延续性地保存记载下来,则必能引导广大农民群众崇德向善、勤奋上进,从而形成正确的荣辱观”。诚如西安市临潼区一村干部所说:“村史记载了村里曾经的模范人物,为大家树立了榜样。”与此同时,让群众一道参与述史编史,也提高了他们的归属感和社会责任感。从这个意义上说,村民参与的过程也是一个陶冶情操、凝聚人心的过程。
有人说,村民自己写成的村史,感觉是朵野花,但不是野史。为什么?因为每个村民都是这个村发展变化的见证人,他们耳闻目睹,他们与自己的村曾经同甘苦共命运,并用自己最朴素的语言,最真实的时间、地点、人物,反映了当时最真实的情况。这样编写村史,自是一项民乐、民愿、民享的民心工程。这样的村史,可亲可信,能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份无可替代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著名作家沈从文先生曾经说过:“一个士兵要么战死沙场,要么回到故乡。”对于沈从文来说,故乡是港湾,是背在身上的行囊,是土生土长的情愫,是挥之不去的依托。在他看来,故乡庇护的不仅是自己的身体,更是自己的灵魂。如果说,乡村是人们最贴近最亲近的故乡,那么,村史里自有着维系人们情感的灵魂。
留下“乡土印记”
据媒体报道,近一年来,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胡王村村委会组织热心村民编写了《胡王村简编村史》,内容分为建制志、农业志、工商业志、乡村建设志、教育志、人物志、民俗志、神话与传说志等篇章,村民拍手叫好。在我国,村是最小的行政单位。然而,说到中国官方的各种地方志,一般只限于区县一级,乡村很少有史志。事实上,无论是提供更明晰的历史路径,还是提供更广阔更深厚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参照,补上村史这一基础性环节有百利而无一害。
30多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乡村社会快速进入城市化轨道,当大量村庄面临城市化改造而消失时,留下“乡土印记”成为萦绕在农民心头的情愫。何况,农村许多故事靠口耳传下来,随着老一辈人的离去,这些传说便会逐步失真甚至消失,唯有形成文字才可以一直传下去。
每一个村虽说地域有大小,人口有多少,历史有长短,但必定有属于自己的历史沿革,有属于自己的精彩故事。若能“把遗散在村里的历史文化、风情人物、变迁演进抢救性、延续性地保存记载下来,则必能引导广大农民群众崇德向善、勤奋上进,从而形成正确的荣辱观”。诚如西安市临潼区一村干部所说:“村史记载了村里曾经的模范人物,为大家树立了榜样。”与此同时,让群众一道参与述史编史,也提高了他们的归属感和社会责任感。从这个意义上说,村民参与的过程也是一个陶冶情操、凝聚人心的过程。
有人说,村民自己写成的村史,感觉是朵野花,但不是野史。为什么?因为每个村民都是这个村发展变化的见证人,他们耳闻目睹,他们与自己的村曾经同甘苦共命运,并用自己最朴素的语言,最真实的时间、地点、人物,反映了当时最真实的情况。这样编写村史,自是一项民乐、民愿、民享的民心工程。这样的村史,可亲可信,能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份无可替代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著名作家沈从文先生曾经说过:“一个士兵要么战死沙场,要么回到故乡。”对于沈从文来说,故乡是港湾,是背在身上的行囊,是土生土长的情愫,是挥之不去的依托。在他看来,故乡庇护的不仅是自己的身体,更是自己的灵魂。如果说,乡村是人们最贴近最亲近的故乡,那么,村史里自有着维系人们情感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