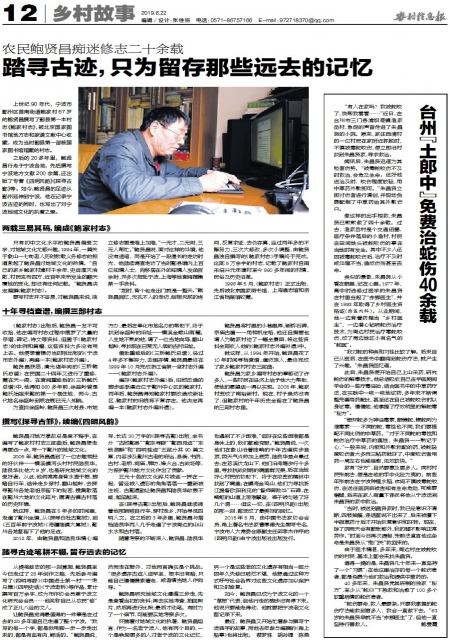农民鲍贤昌痴迷修志二十余载
踏寻古迹,只为留存那些远去的记忆
上世纪90年代,宁波市鄞州区首南街道鲍家村67岁的鲍贤昌撰写了鄞县第一本村志《鲍家村志》,被北京国家图书馆地方志和家谱文献中心收藏,成为当时鄞县第一部被国家图书馆馆藏的村志。
之后的20多年里,鲍贤昌行走于宁波各地,先后撰写宁波地方文献200余篇,还出版了专著《四明风韵》《探寻古鄞》等。如今,鲍贤昌的足迹从鄞州延伸到宁波,他在记录宁波古迹的同时,也写出了对宁波地域文化的执著之爱。
两载三易其稿,编成《鲍家村志》
只有初中文化水平的鲍贤昌偏爱文学,对地域文化尤感兴趣。1994年,一篇关于象山一七旬老人历时数载义务修志的报道激起了鲍贤昌对地域文化的热情。“自己的家乡鲍家村建村千余年,史迹湮灭消散,村民流布四方,近百年来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却没有任何记载。”鲍贤昌决定编撰《鲍家村志》。
要写村志并不容易,对鲍贤昌来说,独立修志更是难上加难,“一无才,二无财,三无人帮忙。”鲍贤昌说,面对这样的处境,他没有退缩,而是开始了一段漫长的走访时光,他陆续调查走访了当时鄞县境内上百位知情人士,向移居在外的知情人发函百余封,并多次赶赴宁波、上海等地查阅搜集第一手资料。“那时,背个包走出门就是一整天。”鲍贤昌回忆,无孔不入的走访、刨根究底的询问,反复求证、去伪存真,经过两年多的不懈努力,三次大修改,多次小调整,由鲍贤昌独自撰写的《鲍家村志》手稿终于完成。这部5万余字的村志,记载了鲍家村自南宋绍兴元年建村至今860多年间的村情、民俗及历史沿革。
1996年5月,《鲍家村志》正式出版,先后被北京国家图书馆、上海通志馆和浙江省档案馆收藏。
十年寻档查谱,编撰三部村志
《鲍家村志》出版后,鲍贤昌一发不可收拾,他在编写村志过程中搜罗了大量的宗谱、碑记、诗文等资料,但囿于《鲍家村志》的体例和篇幅,这些资料大多没有用上去。他便想着模仿当时刚出版的《宁波市志外编》,再编一本《鲍家村志外编》。
鲍贤昌获悉,清光绪年间的《三桥鲍氏总谱》在民国二十四年又进行了重修,藏在天一阁。在查阅重修后的《三桥鲍氏总谱》中,他得知860多年前,徐盛岭曾是鲍氏始祖来鄞的第一个居住地,而今,古代地名徐盛岭到底在哪已无人知晓。
为查找徐盛岭,鲍贤昌三次赴县、市地方办,最后在奉化市地名办的帮助下,终于找到徐盛岭的旧址——横溪金峨山南麓。人生地不熟的他,请了一位当地向导,翻山越岭,寻找现在已荒无人烟的古村旧址。
借助重修后的《三桥鲍氏总谱》,经过4年多不懈努力,去粗存精,鲍贤昌最终在1999年10月完成浙江省第一部村志外编——《鲍家村志外编》。
编好《鲍家村志外编》后,旧城改造的脚步逐渐逼近位于鄞州中心区的鲍家村。两年后,鲍贤昌得知鲍家村要改造成新社区,鲍家村的旧貌将不复存在。他决定再编一本《鲍家村志外编补遗》。
鲍贤昌将村里的小巷里弄、断桥石碑、宗庙古匾一一用相机定格,他还自掏腰包请人为鲍家村绘了一幅全景图,将这些资料全部收入他的《鲍家村志外编补遗》中。
就这样,从1994年开始,鲍贤昌花了10年时间寻档查谱、遍访族人,最终完成了家乡鲍家村村志三部曲。
鲍贤昌为家乡编写村志的事感动了许多人,一些村民在经济上给予他大力帮助,使他的愿望逐一得以实现。2005年,鲍家村变成了南裕新村。现在,村子虽然没有了,但鲍家村的千年历史全留在了鲍贤昌的三部村志里。
撰写《探寻古鄞》,续编《四明风韵》
鲍贤昌对地方掌故总是爱不释手,在编写了鲍家村村志三部曲后,鲍贤昌想走得更远一点,写一下鄞州的地域文化。
2005年,鲍贤昌遇到了一位志趣相投的好伙伴——横溪镇河头村村民陆良华。陆良华比他大9岁,也是研究地域文化的爱好者。从此,他俩常常身背水壶干粮、脚踏自行车,结伴走乡穿村、翻山越岭,去探寻鄞州各地老祖宗留下的秘密,搜集散落在鄞州大地的文化碎片,摸清古镇古村落的历史环境。
就这样,鲍贤昌在5年多的时间里,走遍了鄞州全境,从《探寻白杜古鄞城》,到《五百年前宁波城》《海疆雄镇大嵩城》,鄞州各地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2012年,由鲍贤昌和陆良华精心编写、长达30万字的《探寻古鄞》出版,全书分“古城鄞县”“鄞东寻踪”“鄞西觅迹”“东钱湖畔”和“四明胜迹”五部分共90篇文章,内容涉及鄞州古老的府治、县衙、书院、古村、老桥、祠庙、牌坊、烽火台、古战场等,为保护鄞州地方文化作出了贡献。
五光十色的文化碎片被逐一拼在一起,曾经被人遗忘的角角落落一一重新被注视,古鄞遗韵让鲍贤昌和陆良华欲罢不能,越陷越深。
在《探寻古鄞》出版后,鲍贤昌继续骑着他那辆破自行车,穿村走乡,开始寻觅四明人文。在之后的3年多里,鲍贤昌与搭档陆良华两人几乎走遍了宁波周边的山山水水和古村落。
随着考察的不断深入,鲍贤昌、陆良华也遇到了不少困难,“但好在这些困难都是身体上的,我们都能克服。”鲍贤昌说,一次他们在象山沿着陡峭的千年古道疾步登顶,因天气炎热加上疲劳,陆良华差点晕过去;在慈溪伏龙山下,他们沿海塘步行十多里,寻找抗战时期的碉堡群无果,后在当地好心村民的协助下,终于在浓密的橘林中找到了碉堡;在镇海金鸡山,他们为寻找浙江提督欧阳利见的“督师御敌处”石碑,在崎岖的山道上艰难攀登,裤子被勾破了好几个洞……但这一切,在《四明风韵》出版的那一刻,都变成了最美好的回忆。
2015年5月,由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甬上著名书法家曹厚德先生题写书名,宁波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邵孝杰作序的《四明风韵》由宁波出版社出版发行。
踏寻古迹笔耕不辍,留存远去的记忆
从提笔修志的那一刻算起,鲍贤昌至今已走过了25年创作之路,先后参与编写了《四明寻踪》《中国进士第一村——走马塘》《四明史话》《宁波老桥》等作品,累计撰写百万余字,成为市作协会员兼宁波文化研究会会员……他笑称自己从农民“修”成了正儿八经的文人。
让鲍贤昌觉得最值得的一件事是在过去的20多年里自己走遍了整个宁波。“我写的每一个字,都是我用脚一步一步走出来的,都是有血有肉,鲜活的。”鲍贤昌说,然而走在野外,对他而言确实是个挑战。“很多遗存古迹人迹罕至,根本没有路,只能自己慢慢摸索着走,或者请当地人作向导。”
鲍贤昌研究地域文化遵循三步走,先是查看当初的资料;再去实地考查,拍回照片,然后再进行比照;最后才动笔。有时为了一个细节,可能要实地考察多次。
怀揣着对地域文化的执著,鲍贤昌坦言,作为一名老宁波人,他有两个目的,一个是唤起更多的人对老宁波的文化记忆,另一个是这些老的文化遗存有相当一部分因年久失修已破烂不堪,他想通过这种方式呼吁社会各界对这些文化遗存加以保护和及时修复。
如今,鲍贤昌已成为宁波文化的一个“草根”代表,但他行走的脚步没有停下来。他说只要能走得动,他就要把宁波老文化都记录下来。
最近,鲍贤昌又开始忙着参与撰写宁波庙宇的故事,而他去年参与编撰的《甬上船事》也将出版。 蔡梦珠 胡孙婕 陈燕
之后的20多年里,鲍贤昌行走于宁波各地,先后撰写宁波地方文献200余篇,还出版了专著《四明风韵》《探寻古鄞》等。如今,鲍贤昌的足迹从鄞州延伸到宁波,他在记录宁波古迹的同时,也写出了对宁波地域文化的执著之爱。
两载三易其稿,编成《鲍家村志》
只有初中文化水平的鲍贤昌偏爱文学,对地域文化尤感兴趣。1994年,一篇关于象山一七旬老人历时数载义务修志的报道激起了鲍贤昌对地域文化的热情。“自己的家乡鲍家村建村千余年,史迹湮灭消散,村民流布四方,近百年来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却没有任何记载。”鲍贤昌决定编撰《鲍家村志》。
要写村志并不容易,对鲍贤昌来说,独立修志更是难上加难,“一无才,二无财,三无人帮忙。”鲍贤昌说,面对这样的处境,他没有退缩,而是开始了一段漫长的走访时光,他陆续调查走访了当时鄞县境内上百位知情人士,向移居在外的知情人发函百余封,并多次赶赴宁波、上海等地查阅搜集第一手资料。“那时,背个包走出门就是一整天。”鲍贤昌回忆,无孔不入的走访、刨根究底的询问,反复求证、去伪存真,经过两年多的不懈努力,三次大修改,多次小调整,由鲍贤昌独自撰写的《鲍家村志》手稿终于完成。这部5万余字的村志,记载了鲍家村自南宋绍兴元年建村至今860多年间的村情、民俗及历史沿革。
1996年5月,《鲍家村志》正式出版,先后被北京国家图书馆、上海通志馆和浙江省档案馆收藏。
十年寻档查谱,编撰三部村志
《鲍家村志》出版后,鲍贤昌一发不可收拾,他在编写村志过程中搜罗了大量的宗谱、碑记、诗文等资料,但囿于《鲍家村志》的体例和篇幅,这些资料大多没有用上去。他便想着模仿当时刚出版的《宁波市志外编》,再编一本《鲍家村志外编》。
鲍贤昌获悉,清光绪年间的《三桥鲍氏总谱》在民国二十四年又进行了重修,藏在天一阁。在查阅重修后的《三桥鲍氏总谱》中,他得知860多年前,徐盛岭曾是鲍氏始祖来鄞的第一个居住地,而今,古代地名徐盛岭到底在哪已无人知晓。
为查找徐盛岭,鲍贤昌三次赴县、市地方办,最后在奉化市地名办的帮助下,终于找到徐盛岭的旧址——横溪金峨山南麓。人生地不熟的他,请了一位当地向导,翻山越岭,寻找现在已荒无人烟的古村旧址。
借助重修后的《三桥鲍氏总谱》,经过4年多不懈努力,去粗存精,鲍贤昌最终在1999年10月完成浙江省第一部村志外编——《鲍家村志外编》。
编好《鲍家村志外编》后,旧城改造的脚步逐渐逼近位于鄞州中心区的鲍家村。两年后,鲍贤昌得知鲍家村要改造成新社区,鲍家村的旧貌将不复存在。他决定再编一本《鲍家村志外编补遗》。
鲍贤昌将村里的小巷里弄、断桥石碑、宗庙古匾一一用相机定格,他还自掏腰包请人为鲍家村绘了一幅全景图,将这些资料全部收入他的《鲍家村志外编补遗》中。
就这样,从1994年开始,鲍贤昌花了10年时间寻档查谱、遍访族人,最终完成了家乡鲍家村村志三部曲。
鲍贤昌为家乡编写村志的事感动了许多人,一些村民在经济上给予他大力帮助,使他的愿望逐一得以实现。2005年,鲍家村变成了南裕新村。现在,村子虽然没有了,但鲍家村的千年历史全留在了鲍贤昌的三部村志里。
撰写《探寻古鄞》,续编《四明风韵》
鲍贤昌对地方掌故总是爱不释手,在编写了鲍家村村志三部曲后,鲍贤昌想走得更远一点,写一下鄞州的地域文化。
2005年,鲍贤昌遇到了一位志趣相投的好伙伴——横溪镇河头村村民陆良华。陆良华比他大9岁,也是研究地域文化的爱好者。从此,他俩常常身背水壶干粮、脚踏自行车,结伴走乡穿村、翻山越岭,去探寻鄞州各地老祖宗留下的秘密,搜集散落在鄞州大地的文化碎片,摸清古镇古村落的历史环境。
就这样,鲍贤昌在5年多的时间里,走遍了鄞州全境,从《探寻白杜古鄞城》,到《五百年前宁波城》《海疆雄镇大嵩城》,鄞州各地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2012年,由鲍贤昌和陆良华精心编写、长达30万字的《探寻古鄞》出版,全书分“古城鄞县”“鄞东寻踪”“鄞西觅迹”“东钱湖畔”和“四明胜迹”五部分共90篇文章,内容涉及鄞州古老的府治、县衙、书院、古村、老桥、祠庙、牌坊、烽火台、古战场等,为保护鄞州地方文化作出了贡献。
五光十色的文化碎片被逐一拼在一起,曾经被人遗忘的角角落落一一重新被注视,古鄞遗韵让鲍贤昌和陆良华欲罢不能,越陷越深。
在《探寻古鄞》出版后,鲍贤昌继续骑着他那辆破自行车,穿村走乡,开始寻觅四明人文。在之后的3年多里,鲍贤昌与搭档陆良华两人几乎走遍了宁波周边的山山水水和古村落。
随着考察的不断深入,鲍贤昌、陆良华也遇到了不少困难,“但好在这些困难都是身体上的,我们都能克服。”鲍贤昌说,一次他们在象山沿着陡峭的千年古道疾步登顶,因天气炎热加上疲劳,陆良华差点晕过去;在慈溪伏龙山下,他们沿海塘步行十多里,寻找抗战时期的碉堡群无果,后在当地好心村民的协助下,终于在浓密的橘林中找到了碉堡;在镇海金鸡山,他们为寻找浙江提督欧阳利见的“督师御敌处”石碑,在崎岖的山道上艰难攀登,裤子被勾破了好几个洞……但这一切,在《四明风韵》出版的那一刻,都变成了最美好的回忆。
2015年5月,由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甬上著名书法家曹厚德先生题写书名,宁波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邵孝杰作序的《四明风韵》由宁波出版社出版发行。
踏寻古迹笔耕不辍,留存远去的记忆
从提笔修志的那一刻算起,鲍贤昌至今已走过了25年创作之路,先后参与编写了《四明寻踪》《中国进士第一村——走马塘》《四明史话》《宁波老桥》等作品,累计撰写百万余字,成为市作协会员兼宁波文化研究会会员……他笑称自己从农民“修”成了正儿八经的文人。
让鲍贤昌觉得最值得的一件事是在过去的20多年里自己走遍了整个宁波。“我写的每一个字,都是我用脚一步一步走出来的,都是有血有肉,鲜活的。”鲍贤昌说,然而走在野外,对他而言确实是个挑战。“很多遗存古迹人迹罕至,根本没有路,只能自己慢慢摸索着走,或者请当地人作向导。”
鲍贤昌研究地域文化遵循三步走,先是查看当初的资料;再去实地考查,拍回照片,然后再进行比照;最后才动笔。有时为了一个细节,可能要实地考察多次。
怀揣着对地域文化的执著,鲍贤昌坦言,作为一名老宁波人,他有两个目的,一个是唤起更多的人对老宁波的文化记忆,另一个是这些老的文化遗存有相当一部分因年久失修已破烂不堪,他想通过这种方式呼吁社会各界对这些文化遗存加以保护和及时修复。
如今,鲍贤昌已成为宁波文化的一个“草根”代表,但他行走的脚步没有停下来。他说只要能走得动,他就要把宁波老文化都记录下来。
最近,鲍贤昌又开始忙着参与撰写宁波庙宇的故事,而他去年参与编撰的《甬上船事》也将出版。 蔡梦珠 胡孙婕 陈燕